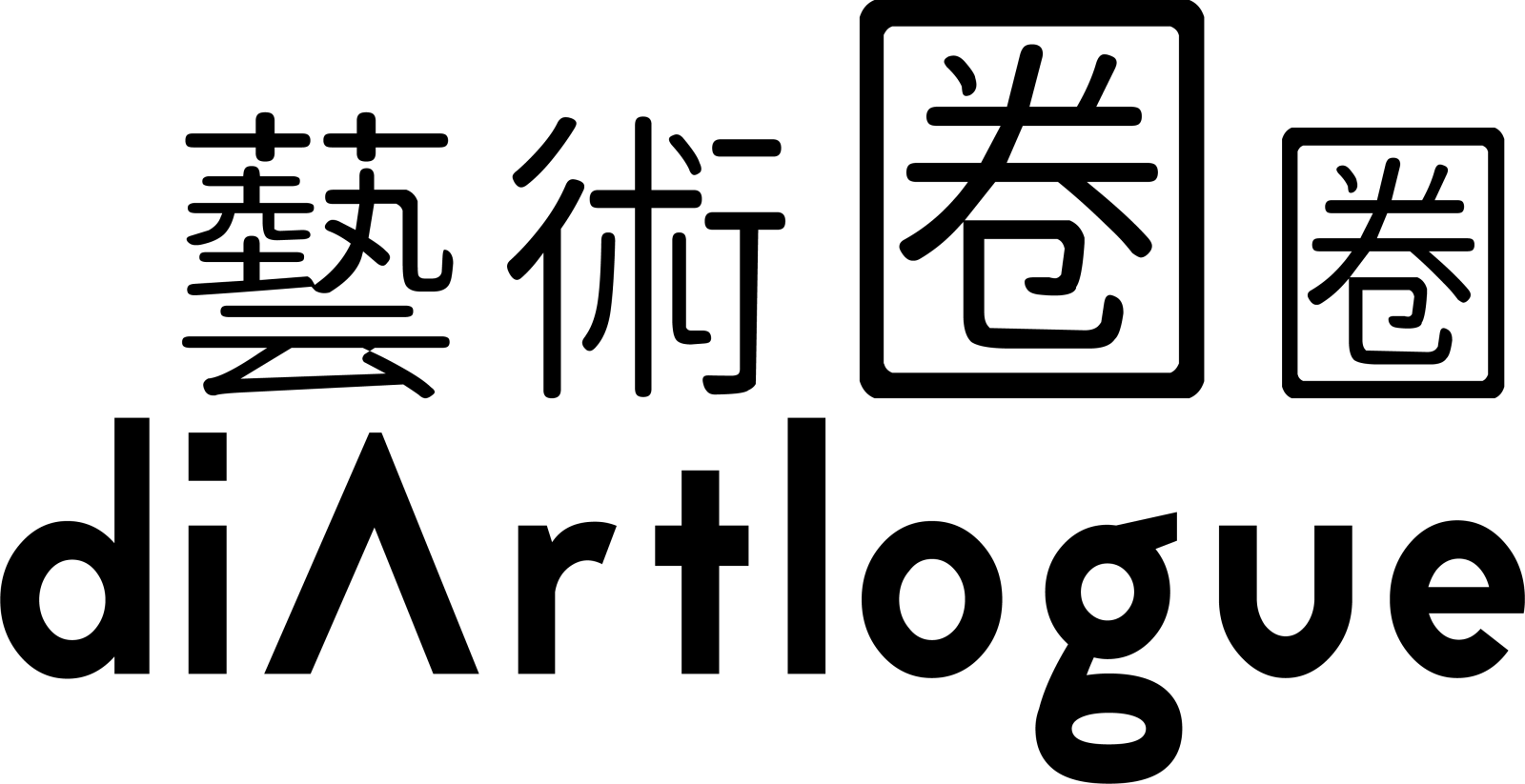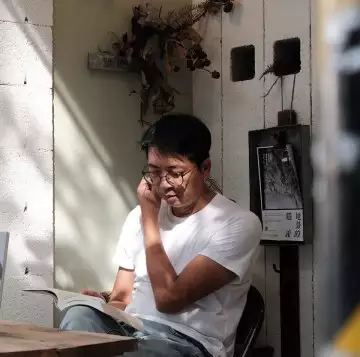- 2025-10-10 12:59:00
文|黃湯姆
二○二二年八月某夜,永翠路看顧完父母,我偷偷騎了機車過大漢溪,回到那條街道,看見某人的窗子。別傻了,我知道這不可以,我知道這很該死,一眼我就離開,一秒我就離開。回程二度過大漢溪時,我想著,再撐過三次療程就好,完成父親的化療,我就可以回去楛柃腳,結束這一切太絕望、太哀傷的河流。
這是徹底分離後,唯一一次我自己去到那條街道,像是被判決了的懲罰,從此之後,楛柃腳的隱喻就不曾從我的腦海抹去。
最初是那年三月,拍完雙連大溝與好土書店後,我建議公視《藝術很有事》拍攝團隊跟我去城林濕地。從日月亭停車場開始步行,沿途十來棵苦楝樹、落花淡紫。步行能夠最接近舊日楛柃腳聚落位址處,猶距離八十公尺遠。
因為詩的緣故,我抵達此地。「你不奢望重見/沙洲上的樹是幻覺」。我無法確認確切位址,只能憑弔:是的,有座村子消失了,有家消失了,有人消失了;最老的、用以命名地方的那棵苦楝早就消失了。
大漢溪中、現今城林人工濕地內,過去曾存在一處河心沙洲與農業聚落,村名楛柃腳,從日治初期台灣堡圖至一九七四年聯勤萬分之一地形圖皆有標示,隸屬板橋庄/街/鎮/市治下。一九六三年葛樂禮颱風後,空軍航照可見楛柃腳受洪水包夾、田地流失;再比對七○年代末林務局航攝影像,楛柃腳田地與屋舍皆已消失,僅存大規模河沙開採形成的坑洞與砂石車路徑。
一九八五年的經建版地形圖上,已經沒有楛柃腳的地名了,九○年代台北地區防洪計畫第三期工程全部完竣,兩岸大堤連延。就像大安溪中的新庄子沙洲一樣,因築堤而遷徙,因大水而消失,今人已無法想像,河流中曾有的村庄,土地神祇與祖先記憶隱沒水流中。
世界本就是由傷構成的
苦戀沙洲
地祇浮沉
遇見你是一生最重要的事
錯失是一世河流的必然
〈浮復地〉是我的哀悼處,我與某人關係的所在,終將沉沒之地。
我們站定拍攝處,是另一處新的考古/犯罪現場,高灘地被棄置大量建築廢棄物。從磨石子地板殘片、馬賽克磁磚拼貼浴缸殘片、TR紅磚、壓在磚石下的扁平矽利康罐判斷,可能一間或數間不知何處、最早興建於日治時期的老宅,在晚近年代間被拆除、被非法傾倒。
五十年前,有村落隱沒;晚近不久,則有人廢墟填河。
在步行能及的範圍內,停著一台無人駕駛的怪手與挖掘中的坑洞,所見皆河川沉積壤土。如果再往前、如果再往下挖,會不會還存在什麼?
《藝術很有事》拍攝團隊最早曾提議至大甲拍攝,我因故未允。無法啟齒,當時我處於無法返家甚至無法接電話的狀態,但二○二二年初,命運把我的家鄉一夕北遷。
我請他們訪問父母,因為攝影作業需求,故事在一早上被重覆講述多次,浮現更多我未曾聽聞的記憶細節,甚至必須修正此前發表於《地理學報》的〈地理書寫筆記〉內容若干。是George Steiner的書名,《勘誤表:審視後的生命》(Errata: An examined life),我希望專欄的書寫能夠及於萬一。
美國國家檔案館典藏有太平洋戰爭期間美國陸軍航空隊對台偵察照相,可當我在典藏中找到唯一一次垂直拍攝到我的家鄉,已經是戰爭結束十多年後。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美軍一架RB-50照相偵察機,掠過了西海岸平原。
當天所攝航照中,大安溪兩岸可見舊日的沖積扇流跡,溪中當時有一座沙洲島,比對日治中期五萬分一地形圖,島名新庄子。二○年代火炎山堤興築後,河道上的新庄子沙洲大批居民遷徙,部分遷往北岸的西勢(建興)與南岸的田心子,美軍航拍之時,島上仍有大面旱作。
一九六三年,同一場颱風釀成社尾堤防潰堤,大安溪南岸的溪埔子至下大安嚴重受災,家鄉稱這場災害為甲安大水,災後省政府重劃溪南農地,成為棋盤坵塊。
父親於一九六○年北上學藝。一九六三年,是他的父親寫批予伊(毋是親戚敲電話講,這是第一筆勘正),甲安大水後有新修水路的工程,我父親回鄉參與,自此留在大甲。從美麗的沖積扇流跡到抹平後重劃的方整棋盤,他即是此間甲安地景的營造者之一。
也因為彼時後厝子電話並未普及,才會有《文學理論倒讀》中寫過的,他的祖父在車頭等他好多天的事,老人只能推測少年返家的可能時間。工程結束後父親應召入伍,要待到災後第十年,他才會在大甲街遇見我的母親。
甲安大水時,田心子的少女並未跟庄內大多數的小孩一樣,至大甲街避難,她跟她的父母留在田心子,水勢一度危及人身。災後交通中斷多時,仰賴軍方直昇機運補。關於新庄子——那座曾經存在於大安溪中的沙洲島的故事,我要她再說一次,為兒子的專題再說一次。
《地理學報》中的版本是:「我問母親,她少女時從田心子往北邊望,溪中央是不是有一粒島。憨囡仔,你哪會知影。母親說當時沙洲上多種植甘蔗與花生,雖無人居住,但仍留有一座舊日土地公廟。她說起她表姐的事,表姐去北岸的建興作新婦仔,每每受苦逃離,但不敢返家,就躲在土地公廟。」
母親說,那是她堂姐,這是第二筆勘正。
容我繼續引述前作:「快門之後又六十年,建築覆蓋台地西麓,高速公路穿過大甲東,鐵砧山北麓持續崩塌,父親的後厝子一帶,田疇依舊。開始讀圖的那些年,常夢見找不到回家的路,現世如沙洲,人浮復水流中。那場大水六年前,河的第三條岸上,我曾找到那座土地公廟,之後的Corona間諜衛星拍攝中,連同新庄子皆不再存在。」
「時光無路,我想著少女是否已經返家。」
所以,當著攝影機,我才會堅持問我母親,這個對我而言無比重要的問題:
——你有恰彼位堂姐聯絡無。
——聽恁大姨講,伊幾年前過身。
——嗯,伊後來敢有幸福。
——翁婿做工觸到高壓電死去,後來擱嫁一擺。
——可是,可是伊後來敢有幸福。
母親想了想,說:應該是有吧。
我的母親啊,為我述說了無數次地景與其間流逝的母親,她永遠不會理解我寫下來的文學的或非文學的文字,以及這些年兒子腦海裡遭遇到的困難。浮復地之於我,是家的不可能歸返,是家的不可能建築,這樣的人,怎麼有資格奢望幸福呢。
應該是拍攝楛柃腳的前後,我最後一封信給某人,提及我無法返家的事,直到秀芃、育育載我渡河,直到父親就醫、舉家北遷。「經歷諸多我略為明白,無論我流落何方,無論景觀與記憶如何改易,無論我能否歸返,你就是我的故鄉,你就是我一個人的故鄉。」
寄出之後我才理解到,這封信不會被任何人打開,這段文字不會被閱讀。有些地表,更早之前就已經沉沒,沖積平原上,再往前、再往下挖,或許還存在著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