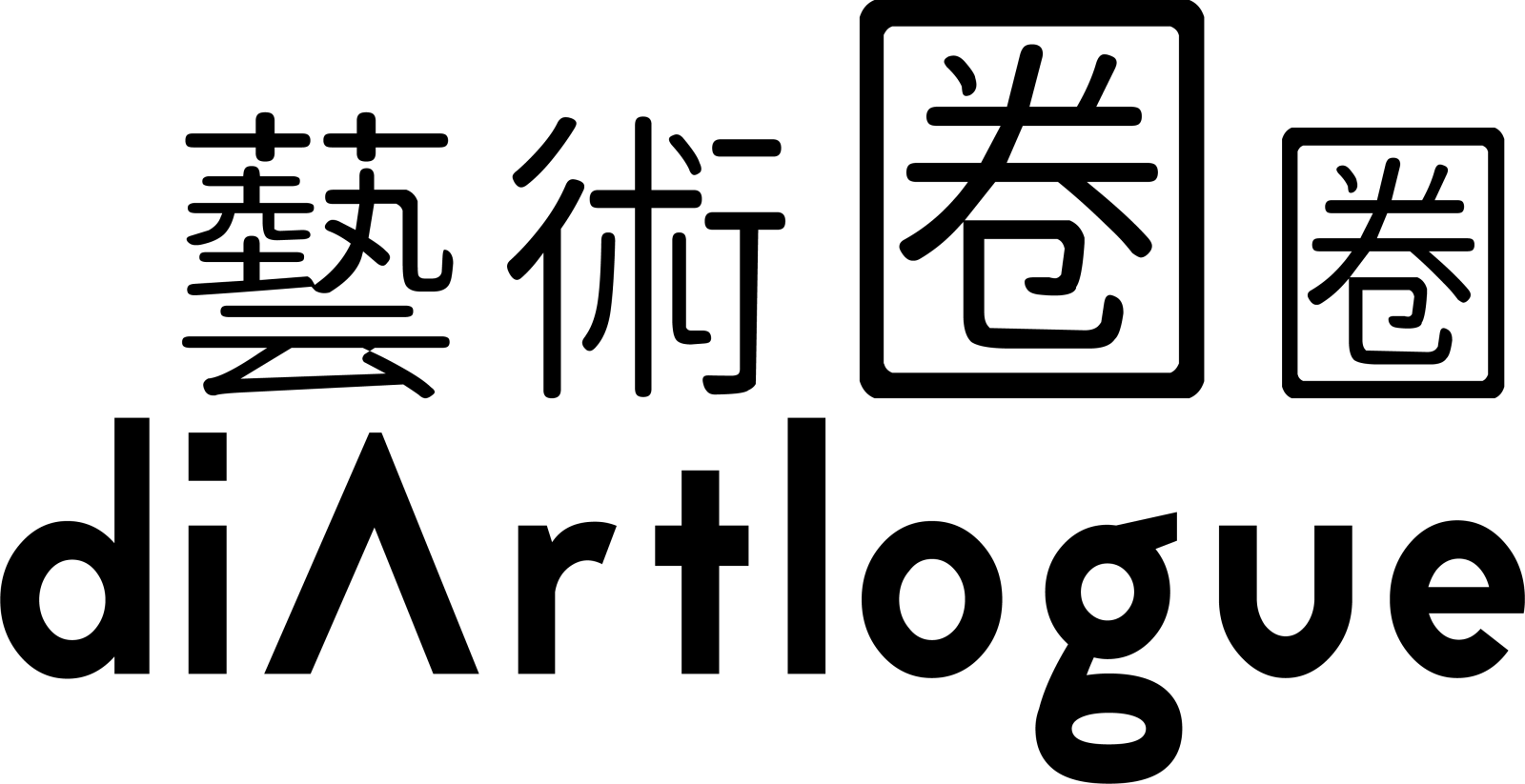- 2025-09-28 16:48:00
文|劉佳旻
這是一個寫作者與企劃編輯者都曾分別想喊停的專欄。為此,在專欄之前,或許得提供讀者閱讀的預備。
*
「寫作就是活著,活著就是寫作。」詩人黃湯姆(下稱詩人黃)多次說過這話。我曾問,那麼寫作與活著,孰先孰後?他反應木然,彷彿不能理解這個問題——「我不知道。那不是我能判斷的事。」
如果寫作等於活著,不寫的時候是喪屍嗎?我繼續問。一邊走路,他想了想後點頭:「也許喔。」
若是如此,長年除了自費出版沒有正式文學發表的這位寫作之人,在過去這兩年多一點的時間裡,或許一直處在「並未活著」的狀態(一種薛丁格式的活著?)。
一個寫作之人不寫作的時候,幾乎等於連路都無法走。那無能行走的蹣跚,旁人看來,彷彿在情感構成的翻覆地景中日日跌跤。一開始還想站起來、掙扎著踏出步伐,但慢慢地,連踏出步伐都艱難;慢慢地,連步履的形狀也難以辨認。
我作為旁觀者,長達兩年的近距離目擊者,看見詩人在情感的地景中反覆折騰,卻看不見絆住他的那些:水來就淹沒於無形的浮復地、寬廣卻困住他的平原,他一再想將自己藏匿其中的、又美又冷的山。還有,那自地心底深處伸出糾纏的夢之藤蔓,糾葛著不能解的憂愁與不能企及的想望——那早已失色的黃昏,多少把傘也阻止不了的雨。
「我們能不能試著透過書寫,將那些崎嶇的地景化為文字,讓惡夢成為敘事?」
*
讓地景成為文字,就偶然地成了一種未曾預想的跨域嘗試。(我從沒這樣問過自己:當跨域成為每個領域都需膜拜的關鍵字眼,我們如何有機會訴諸於實踐?)
詩人黃最後一次出版詩集是2022年,但近十年他投注於航照研究,出版著作四大冊。以一般人來閱讀他的航照專著——我嘗試過,一天大概三篇就是極限。那書寫精煉用力,但,「能不能用更容易閱讀的話來寫?」作為編輯者我曾經問過這位能寫極為動人詩句的詩人/研究者。他說不行,航照判釋就是必須如此,不參雜任何詮釋。
在此專欄裡也能看到一部分這樣的文字。專屬於作者的判釋意識,著手地景為題的散文書寫,自然流露那些彷彿從高空辨識的視角。他以地景書寫情感,彷彿將人生置於地圖上清點。
然而,若細緻地進入閱讀,這個專欄的地點與主題雙軸對應:鹿屈山與苦柃腳、關渡平原與時光鹽場、出租套房與板橋公寓、雙連大溝與好土書店……。這些地景所指涉的物事,包含了求生與尋死、「家」的符號具與符號義如何錯套;而「留戀」與「記憶」又如何彼此互文。
也因而,每個被標誌的地點都存在美夢或惡夢。(雖然對編輯來說每一篇讀來都仿若惡夢。)鏗鏘的地理書寫,必須要讀到最後一篇才能通透那文學與地理交織的可能;而忘不了的、持續糾纏在文句之間的某人,那場秘密的戀情,則注定要在文句中持續徘徊。(這難道不像鬼片裡面,永遠留在房間一角的地縛靈嗎?直至透過書寫打開窗戶,釋放。)
這也是一場十年人生的清點。透過這種清點,所跨的域並非僅止於地理與文學的交織書寫,更是時光與記憶的悖論。我曾對詩人說,「只有寫下來,才會過去。」但「過去」是什麼?這個動詞,說出口難道不比起「書寫」的指涉還要虛無?畢竟,寫作之人無法復返時光,但是,寫作者總是能透過文字返回現場。
於是有了這個專欄。如果那些讓人舉步艱難的記憶化為文字,是否就能立上悼念的碑?如果惡夢有了敘事,是否就能成為一個朝向其他可能性開啟的故事?——這從來就是寫字之人能夠往前走的方式,不是嗎?寫作。只有寫下去。把字疊成磚、疊成那不再讓人跌跤的地面,不管是朝山上、朝谷底、朝河邊、朝海口;朝樹洞,朝記憶深處,朝無言的幽靈,朝無可言說之處。
*
專欄命名「流落的地景」,詩人黃在這個專欄書寫屬於他的記憶圖景,座落於島嶼各方,再訪那些現場。總是嚷嚷不喜旅行的詩人竟能有那麼多記憶流落的所在。
我們希望這個專欄勾勒出了一位創作者背著光的輪廓;放遠看仿若靜止無聲的靜景,拉近卻能看見不斷奮力攀爬與生存的踽踽跡痕:那些痛苦我們都熟識、那些無可安放的困難與跨越不了的山稜,恐怕也都隱存在每個人各自的生命地景。而透過書寫(或任何形式的創作),都有機會迴返故地——儘管此時未能彼時,然而無論何時我們都能選擇在路上——未必通往抵達,當然也能是再次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