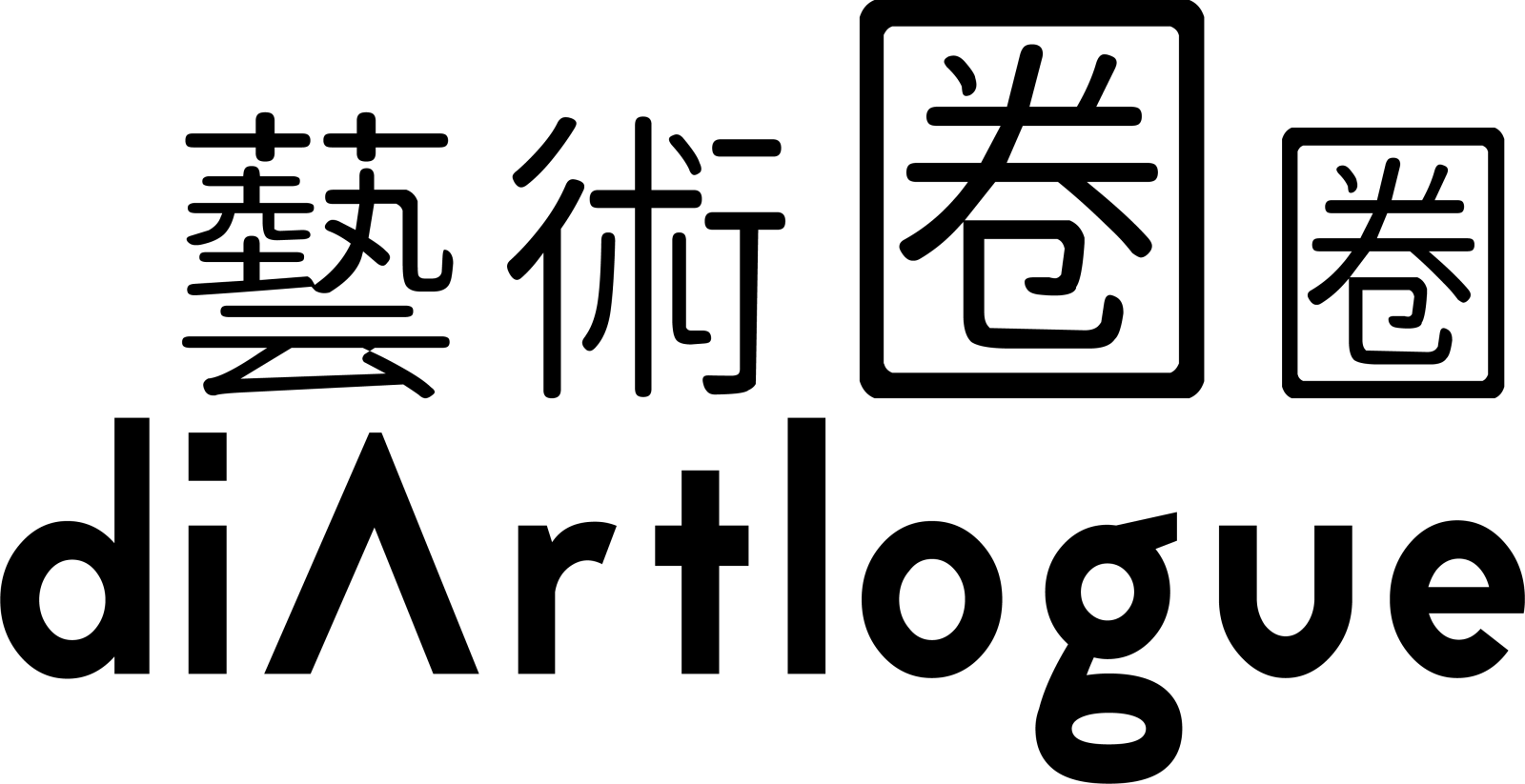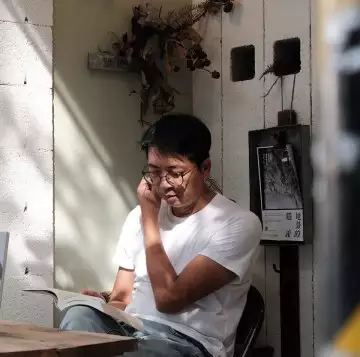- 2025-09-28 17:15:00
文|黃湯姆
入山前一晚,我夢見搬進森林裡的平房,玻璃待擦、山色是抽象的綠。父母要下山走了,交待我好好生活,留在山裡。夢總如此,既像詩又像預言,既直觀又令人廢解。
過去十年來,我鎮日閱讀歷史航照檔案,感情單純。前五年半,專心一意愛著某人;而後五年,儘管有過遺憾而終的新戀情,但經歷漫長的步行與諮商,我不得不承認:因為後五年依然在哀悼某人的離去。歷史航照研究就跟我的社交生活一樣封閉,除卻影像就是大量文獻史料的爬梳,以及不時島嶼遠方的地理實查。
二○二○年,我已經看見並理解南投鹿屈山東北側、加走寮溪源頭,集材作業所形成的奇特放射狀紋理,日後那幀空軍航照還被選為專著《地景的刺點:從歷史航照重返六十年前的臺灣》一書的封面。該書出版時尚未完全解開的謎底是,砍伐下來的木材如何運出?嘉義阿里山森林鐵道林內線有可能曾經北延至此、跨進竹山事業區的地界嗎?
林內線又稱林場線。一般指稱開通於一九一二年的阿里山森林鐵道,是運輸性質的本線,其後才是興築集材功能的各條林內線。林區採伐作業結束後,會拆除林內線鐵軌,並將相關設備及工作小屋移作他線使用,這也使得過往較早的林內線文獻漫漶,可以查詢到的資料中,僅一、二處曾見鹿屈山線之名,前行研究者中,亦唯有陳玉峯提過鹿堀山後線之說。
二○二二年中,我意識到,新的阿里山研究與書寫計畫得追加入山現場調查。利用歷史航照,可以辨識出鹿屈山本線中段,以及後段的鹿屈山南麓部分路型孑遺,但全無路型孑遺的鹿屈山後線,戰時美軍航照中已見的加走寮溪源頭放射狀集材紋理,可供我們定位三○年代集材作業的主柱點位。再結合高程資料,可推算出鹿屈山後線可能的東西兩段。
這種使用歷史航照影像判釋遺址的方法,稱為遙測考古學(Remote Sensing Archaeology)或太空考古學,包括利用當代各種新遙測技術,如紅外光或光達,窺見原本不可、不易見的遺址結構,或利用冷戰時期間諜衛星影像、U2偵察機照相乃至各種形式的歷史航照檔案,重新俯瞰拍攝當下仍可辨識的遺址線形。
透過航照套疊與立體觀測,我計算出可能存在的軌路平臺所在,但遙測考古必須有現地調查確認。換言之,你必須去到鐵軌早已消失、森林又經歷一輪皆伐與全面造林的鹿屈山現場,尋找到哪怕只剩一根軌道釘的證據,所有的推估才能夠成立。
策展人蔡明君介紹我認識老王,為了說服她領我入山,我誇耀:每日三樓好人好室端咖啡上下一樓好土書店五十趟,年輕同事視之為畏途但我皆飛奔;少年時當水泥工,可左右各夾一包五十公斤水泥快跑;當兵在摩步旅兩百旅,精實案後陸軍機動打擊部隊……。但老王只問我是否曾在山上過夜過,我誠實作答。她遂理解我缺乏野外生存能力,一切規劃從零開始。
夸夸其談的另一面,當時我其實已經失去生存意志,惟賴各種虛幻(文學出版)或眼前(雙連大溝與好土的天井)目標度日。短篇小說〈杉池〉,那位消失在鹿屈山的調查者,最後留下一組座標數據,創作概念反映了我的日常工作與腦海妄念。當時新出版的詩集《靜靜的海邊》中,上世紀《海岸山脈》時代的另一人格悄悄浮現:
不要找我
我不想讓人找到小孩說。
我們在這裡好多年好多年哀傷埋沒
山林荒廢所有愛的人
都已與世界無關——〈後記3〉(2022)
幼稚如斯,以為下筆就可以告別,我並不知曉,這只是漫長五年痛苦中的小小一段。
在山裡,我的體能表現超乎預期,下切溪谷、上攀稜線,在岩屑錐與高大芒草間尋找一條曾經的路。在山裡,我比平地開心百倍,與同伴互動、相互支援、無禁忌地吃食饅頭以外的乾糧。在這之前很長一段時期,我每天只吃一樣的東西,單純的東西。
山裡很美、很冷。在沒有訊號的地方,人會格外想打電話;人會想告訴某人:我在哪裡,我很好,你好嗎。
鹿屈山第一次現地調查成果豐碩,除順利尋找到路塹及軌路平臺外,還發現了當時鹿屈山後線的工作據點,日後可能的發展遠超出我的守備範圍,寫完調查日誌後,我已著手開始聯尋幾位考古學者。沒有口述、缺乏文獻的鹿屈山林業生活聚落遺址,該如何利用地面考古方法,精確測繪基地、區分空間機能、清點各種生活跡物,而後重建九十年前,鹿屈山那群林業工作者的大致樣貌呢?
我想知道,他們每天是怎麼生活的。
我感覺很好,大溝在我上山的幾天都很乾淨,未來不是往濁惡裡去。我感覺很好,軌路與生活聚落都可以找得到,在隱喻的世界裡,那小孩就不會再被丟下。我感覺很好,在現實的世界裡,我的確撐得起一家書店;某日早晨,我還先去看了父母才往雙連移動,十足勝任一位人子的角色。而後捷運上,我讀到一篇文章,在我去年曾經徹底關閉的社群媒體上,瞬間從岩壁摔落。在字與字的滑坡間,在句與句的懸崖間,我已了然她沒有寫出的一切。
我想回到鹿屈山。山上我找得到房子住,而山下沒有人在等我。
這是二○二三年初的事了。現實不若電影劇本,可以絕決地調頭,如今我已有許多人事牽絆;我不明白關係,但我們終究是為了什麼活著。當時至今,我們復又進行了六次入山調查,再經過鹿屈山後線聚落遺址,我甚至會指著那幾乎隱沒在腐植層中的廢墟駁坎,對初加入的隊員說:歡迎來到我家。僅管日後延伸的調查涵蓋了日治時期所有林內線曾經之地,但我始終以鹿屈山考古隊命名群組。
同一段時期的事後回望,除了把鹿屈山寫成一首詩外,我並沒從哀悼中走出,我還沒真正活下來。(從遙測考古的視角中,有誰是真正活下來的嗎?)編輯劉告訴我:「寫出來,你才會過去。」是嗎?我該相信你嗎?這句話後我默默嘗試了半年均未果,我離開一種紀律的文學寫作太久太久,遠在我開始閱讀航照檔案之時。半年之後,劉代表藝術圈圈邀稿專欄。可以了嗎?我想了一下,或許吧,我已經無路可走了。
「視角決定了世界,包括時光中我們曾經的作為與所有的可能。」新作《復返阿里山:一場跨時空的立體飛覽,一段失落鐵路的現地追尋》一書如是寫道。時光已不可逆,但人事景光容許我們重新睇看,重新檢驗所有曾經的歧路。
十年之後,起步艱難。「流落的地景」專欄不寫歷史航照,也無關藝術展陳,而是這十年生命裡,曾經關連著我個人情感生活的各處地景,各篇章書寫位址相互對位、連結,楛柃腳、關渡平原、悲傷河流、恐慌森林、雙連大溝、好土書店、失去欒樹的小巷……。我召喚曾經的文字能力,我想看看關係的解答,我想再看看、那敘事可以抵達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