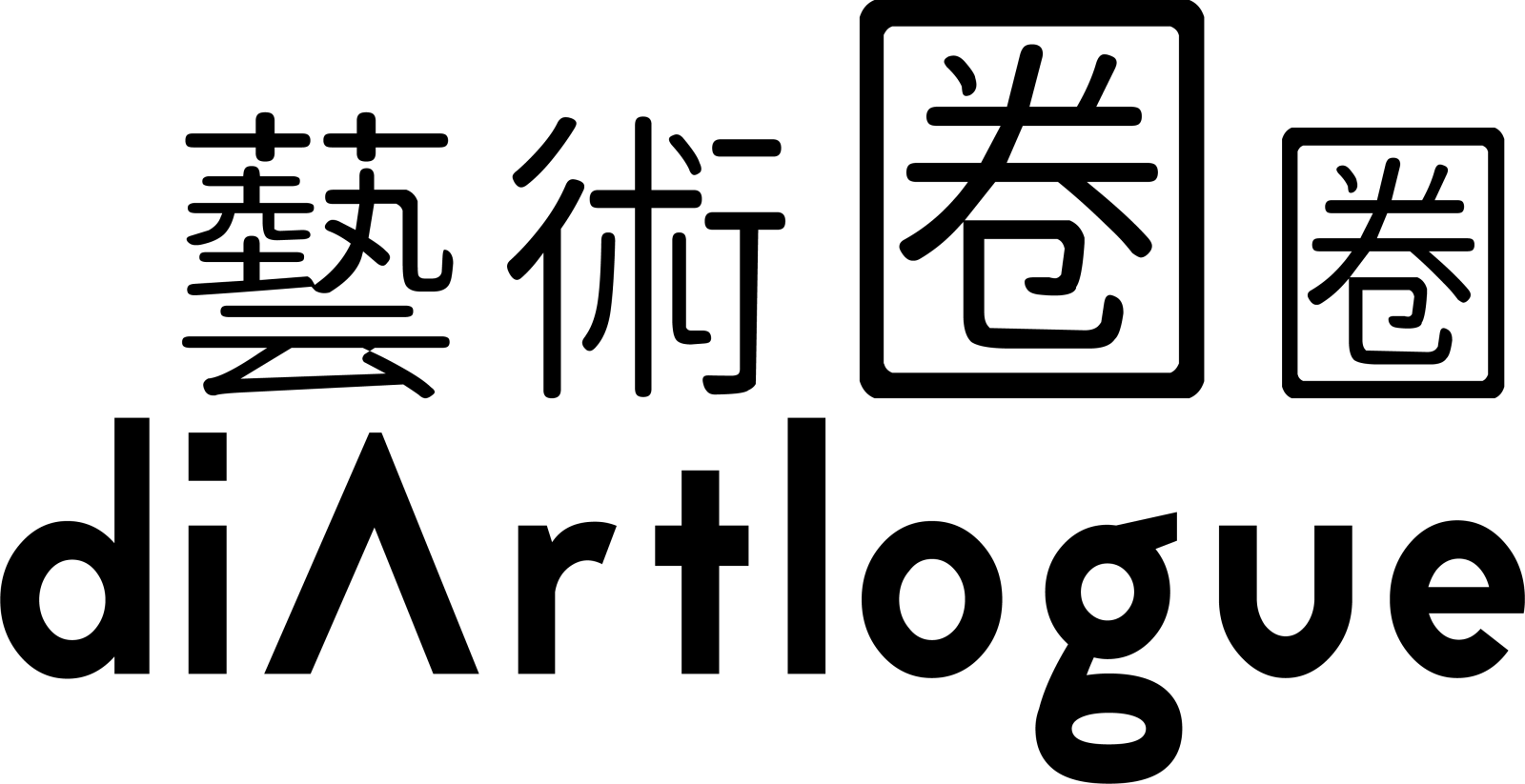- 2025-10-10 15:55:00
文|陳平浩
讓文學在陌生化裡浮現的影音配置:
劉紀彤〈鱸鰻查某說:〉
一反黃大旺此前「黑狼拿卡西」印記的張揚、浮誇、暴動的風格,他這次的作品帶有一種內斂的氣質,或者一種「向內摺疊」的姿勢,以至於這件作品十分緻密,無論符號或意義,皆因體積內縮而濃度提高,需要層層攤展。
相反的,劉紀彤以葉陶為主角的作品〈鱸鰻查某說:〉,則帶有一種層層舒展的、向外延伸的姿勢。

這件作品,座落在另外三位藝術家共同展間之外、獨立出來的另一展間裡:圓弧展牆圍繞而成的偌大空間,一排條凳木椅,被挑高的天窗所透進的日光灑亮,木椅前方則是一面大尺寸螢幕。
這是一個由「窗口」、「螢幕」與「座椅」所構成的空間;一個既有「投影」亦有「日照」的空間,一個「窗」與「螢幕」互為隱喻但又同時分立在場的空間;一個既反黑盒子、也反柏拉圖「洞穴寓言模型」的(反)電影空間。
螢幕上有三位女子,由劉紀彤的三位當代藝術家朋友(李佩瑜、廖煊榛、陳為榛)分別飾演葉陶、葉陶1935年所寫唯一一篇帶有自傳色彩的短篇小說〈愛的結晶〉裡的女主角;以及劉紀彤所引進年輕時造訪過東海花園的當代女性小說家。整部錄像作品,全由這三位女子及其對話所構成,對話圍繞著葉陶這位左翼女子在社會運動中遭遇的、同時也是劉紀彤同代(三一八世代)女性藝術家的性別課題:她與同為戰友的丈夫楊逵之間的關係為何?支援,互補,競爭,分進合擊?婚姻對葉陶而言意味著什麼?婚姻與社運是一組對立的沉重選擇抑或是一種結盟形式?女性的生育是一場革命抑或是對於革命之路的斲斷?在革命挫敗之後如何不斷革命?當楊逵長年囚禁於外島,囚禁於婚姻與家庭裡的葉陶,持家勞動與養兒育女也是不斷革命的轉進形式之一嗎?當代經歷三一八運動浪潮的女性藝術家,與葉陶的距離應該如何丈量?這些皆是劉紀彤在一個以楊逵為主題的展覽裡,透過重探葉陶而提出的性別議題。
更為特別的是,錄像裡三位女子的對話,全以「默片」式的「字幕」或「字卡」形式呈現;而佔據了展場優位的聲音,反而是拍攝現場的「環境音」(收音自影片裡三位女子坐談的郊外環境)。乍看此作似乎有一種,「在一件『讓女性發聲』的作品裡卻『讓女性消音』」的矛盾,然而,劉紀彤的音畫配置,恰好從這一矛盾裡所內含的曲折,轉向「文學如何展覽」的議題。
 「花園裡的一塊磚」展覽(2025,關渡美術館)劉紀彤〈鱸鰻查某說:〉作品局部。圖片來源: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
「花園裡的一塊磚」展覽(2025,關渡美術館)劉紀彤〈鱸鰻查某說:〉作品局部。圖片來源: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
台灣文學界近年常見的文學展覽形式,多半摘錄文學作品的經典段落予以展示,搭配朗讀的影像與聲音。此一形式極可能暗含了一種未被言明的內在邏輯:在一個展場裡,文字是不足的,恐怕「撐不起展場的空間」,所以不得不借助影音予以補充;因此,影音並沒有被當作「影音自身」來思考與部署,而是成為文字的附屬與增補——但正如德希達所言,附屬與增補往往回頭解構了本體。
劉紀彤的作品,恰好透過一種「顛倒的佈置」,讓這個台灣文學展覽一直以來的難題(如果不是沉痾的話),得以彰顯。
這部錄像作品裡的女子對話以字幕呈現。一方面,這讓此件關於「女性聲音」的作品,重現了「女性被消音」的喑啞史;另一方面,它同時提示了:被遮蔽的女性聲音如何在「文字」或「檔案」裡(在劉紀彤這件錄像作品裡則是「小說」),被存留下來。
換句話說,劉紀彤採取了一個反向的手法:刻意讓錄像裡的對話聲音缺席(環境音的保留恰好反襯出對話的無聲),改以從小說文本裡摘錄出來的字句,重新編排,組成了這段女子對話。於是,這件錄像作品的「觀眾」,也在面對「對話以字幕呈現」的同時,蛻變為、或還原為一位「讀者」——「文學」反而在這樣的影音配置裡鮮明地浮現出來。這使影音不再是文學的補充或工具;影音讓文學在陌生化(註13)裡反而鮮明浮現。
尤其,跟黃大旺一樣,不甘心只是「再現」也同時關心「表現」,劉紀彤也不滿足於在展場裡僅只是引述與摘錄文學作品裡的語句,而是更進一步,以她田野研究獲得的知識、既有的問題意識,以及身為藝術家的個人感性來重新編輯這些句子,使其構成一個全新的文本,嵌入錄像的影音文本裡去——與文學作品以文學方式對話、甚至對決,而這恰好才是最文學的。
 「花園裡的一塊磚」展覽(2025,關渡美術館),劉紀彤〈鱸鰻查某說:〉作品局部。圖片來源: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
「花園裡的一塊磚」展覽(2025,關渡美術館),劉紀彤〈鱸鰻查某說:〉作品局部。圖片來源: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
以攝影書寫一種反寫實的左翼寫實主義:
汪正翔〈Missing Parts〉
在劉紀彤的錄像作品中,長椅上比肩並排的三位女子,在影片裡幾乎從頭至尾「背對」觀眾;而樓上另一展間裡的展牆上,展示了多幅葉陶的「正面肖像照」,樓上樓下二者準確地互相對照,甚至還意外地遙遙對照了攝影師與觀念藝術家汪正翔在此一展覽裡的攝影裝置作品〈Missing Parts〉——靈感始自楊逵的「肖像照」。
楊逵作為一位台灣文學家以及左翼社會運動者,有一極為特殊、至今不易企及(若非空前絕後的話)之處:他擁有數量最多的「文學家肖像」。
當楊逵的文學作品被國立編譯館策略性納入中學國文課本、被標誌為「抗日英雄」後,楊逵不只從他被抹除的史頁返回大眾視聽,而且一夕之間聲名大噪,莘莘學子與藝文青年造訪楊逵的東海花園,跡近朝聖,絡繹不絕。當時,相機已漸普及,在這些訪談之間、拜訪之後,留下了大量的「肖像獨照」以及「留念合照」。日後,這些照片集結、收錄於《楊逵影集》這本專書裡(註14)。翻閱這本攝影集,一方面可以指認如今看來位於「文學—政治」光譜上殊異位置甚至對立兩端的文藝青年造訪者,比如白先勇與七等生、比如陳映真與林瑞明;另一方面,亦能發現日後在台灣攝影史佔據一席之地的攝影人,比如黃明川、郭力昕、與謝春德等。
 「花園裡的一塊磚」展覽(2025,關渡美術館)檔案區。左為「東海花園訪客留言本」數位掃描(1977),右為《楊逵影集》(台北:滿里文化工作室,1992)。圖片來源: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
「花園裡的一塊磚」展覽(2025,關渡美術館)檔案區。左為「東海花園訪客留言本」數位掃描(1977),右為《楊逵影集》(台北:滿里文化工作室,1992)。圖片來源: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
汪正翔應邀參與此一以「東海花園」為主題的展覽,面對以楊逵作為主角、以東海花園為背景的海量照片,依其創作自述,設計了一個極為迂迴曲折的創作流程。首先,將大量照片輸入AI處理系統,讓AI讀取它們、以運算去補足相片背景之間的空隙,最後「縫合」相片背景的東海花園地景,意欲獲致一個「完整」的、「全景」的東海花園風景。作品名稱「Missing Parts」,首先即指這些當年沒能入鏡的、照片與照片之間遺失的部分。然而,最終展場地面上的「東海花園等高線地圖」,乃是此一「AI補遺」程序的「痕跡」。之所以說是「痕跡」,乃因汪正翔稍後從「風景」轉向了「肖像」:當AI處理照片背景時,他發現前景的人物影像被運算所牽動、波及、變異;沿著此一影像流變,汪正翔先以新近出現的「靜照動態化」AI程式,讓照片裡的楊逵及其親友「動起來」、近似於「reel短影片」,再以相機重新框取與凝固這「短影片」裡的一瞬,使其再度「還原」為一張人物靜照——然而,畫面上的臉孔在這個層疊周折的轉映程序之後,已然面目全非,無以指認。
最末,汪正翔以「風景區觀景解說牌」作為「美術館展覽台」的形式,將前述多重加工的照片展示其上,再一一立於展間內地面上與東海花園地形圖上相應的、當年拍攝的地點。(註15)至此,既有風景照,亦有肖像照;然而,在展場裡作為作品的照片卻二者皆非;最終,「風景」只剩等高線,「肖像」也成了「反肖像」。
觀景台/展覽台向觀眾(或觀光客)許諾一片東海花園風景,但現場只有抽象的、幾何的地形圖;作為台灣文學史與左翼史之「紀錄」與「見證」的楊逵及其親友的照片,經過AI多重處理之後,已然無以辨識——攝影的「寫實性」在此雙重缺席。
原本,東海花園的這批照片,具有高度的「紀錄」與「見證」的寫實性,甚至可以納入左翼的寫實主義攝影系譜。1970年代楊逵的東海花園,藝文青年爭相來訪、吃喝交談,儼然成為一個藝文沙龍(或廟埕);所留下的無論是楊逵肖像或聚會合照的海量攝影作品,都忠實地記錄了一頁1970年代的藝文場景。同時,在戒嚴時代,除了記錄楊逵會晤場景的訪客相機,畫面之外還有白色恐怖特務用以執行監視的相機。不過,這些會晤楊逵的照片似乎也迂迴地,暗中透過「展示」來「反監視」,這些照片似乎在高分貝聲明:「我們沒有密謀甚麼,所以我們光明正大合照。」——但這些聚會裡的文學討論、思想交流、甚至台灣史的重探與左翼理念的散播,本身就是最強力的密謀——而同樣沒入鏡的特務相機及其監視照片,則是另一種Missing Part;以展示來反監視的照片的背面,也是Missing Part。
 「花園裡的一塊磚」展覽(2025,關渡美術館)。近者為汪正翔〈Missing Parts〉,後為黃大旺〈電子音響讀劇《牛犁分家》〉。圖片來源: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
「花園裡的一塊磚」展覽(2025,關渡美術館)。近者為汪正翔〈Missing Parts〉,後為黃大旺〈電子音響讀劇《牛犁分家》〉。圖片來源: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
汪正翔最終的作品,似乎刻意懸置了以楊逵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實踐的攝影寫實主義。這件攝影裝置作品,在補遺與重構東海花園之際,其實骨子裡是在處理一系列充滿張力的影像悖論:「數位」與「底片」、「攝影成像」與「AI造影」、「定格靜照」與「活動影像」、「快照」(snapshot)與「全景」(panorama)……等等,這些無一不是當代攝影論述裡的核心追問——然而,這些關於攝影媒介技術自身的提問,就算沒有東海花園這批照片,似乎也可以在它處被提上議程。
但是,在我看來,汪正翔這些關於當代攝影的追問,其實暗中回頭呼應了或叩問了楊逵東海花園的1970年代,在「回歸現實」(蕭阿勤語)浪潮底下,關於台灣的認同(肖像)、文化(造型)、土地(風景)等彼時開始白熱化的領域裡,關於「何謂本真性」的辯證。此外,儘管最終汪正翔的作品乍看與楊逵無涉、東海花園照片最終只像是藉以思索當代攝影議題的素材;他在展覽座談會上的發言裡卻透露楊逵這位左翼文學家對他這次創作時的思想刺激——楊逵的文學創作與左翼實踐的關係為何?藝術必須為人民服務嗎?台灣對於左翼藝術的設想為何總是「社會主義寫實主義」?那麼蘇聯成立初期的左翼現代主義呢(比如愛森斯坦或構成主義)?日本左翼攝影系譜的前衛刊物《Provoke》,中平卓馬的《為何是植物圖鑑》,以及足立正生的「風景論」紀錄片呢?尤其,重要的攝影理論家大多是左傾知識分子,那麼,怎樣的攝影作品才是左翼的?這些提問,延續了他近年關於當代藝術場域,藝術與政治,攝影與寫實(主義)、與現實(政治)、與真實(效果)之間關係的不斷書寫。(註16)
 「花園裡的一塊磚」展覽(2025,關渡美術館)。汪正翔〈Missing Parts〉作品局部。圖片來源: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
「花園裡的一塊磚」展覽(2025,關渡美術館)。汪正翔〈Missing Parts〉作品局部。圖片來源: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
雖然汪正翔在座談尾聲謙遜自陳:如果這件(逆反台灣寫實主義攝影傳統的)攝影裝置作品能夠刺激觀者思考攝影與社會的關係,那麼已然是一種對楊逵致敬。我認為,這件作品乍看脫離楊逵、實則回返楊逵:由楊逵所啟動但最終乍看無涉楊逵的攝影裝置,動搖了人們既定或預設的觀看框架,讓人進而思索「影像」與「生產它的社會」或「它所影響甚至形構的社會」之間的連結,或被遮蔽的連結。我們可以回憶一下楊逵當年鵲起日本中央文壇的那篇小說〈送報伕〉:除了控訴日本的資本主義以及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的殖民暴力、除了借助小說此一「文學文類」進行左翼實踐外(亦即普羅文學),楊逵在小說裡選擇了「報紙」此一「大眾媒體」作為題材,一個關乎「大眾的浮現及其認知」、關乎「印刷機資本主義」,也關乎「想像共同體」的裝置,已然足以與當代影像社會裡的「媒介技術」問題進行對話。
汪正翔以一件「當代攝影裝置作品」表面上全面取代了一件「應以想像中的文學展覽形式出現的作品」,一方面其實在核心地帶「以反攝影寫實取回『寫實是如何被框構的』此一Missing Parts」回應了楊逵以小說進行的左翼與文學的辯證,另一方面也刺激我們去想像另一種文學展示——一種乍看「反文學」,但其實也許反而「更加文學」的展覽。這讓我們想起一個已然被實現的案例:近年被重新發掘與發現的黃華成。
如果,汪正翔這件立基於「攝影本體論」而佇立於一個台灣文學展覽裡的作品,讓我們可能想起的是台灣戰後1960年代《現代文學》雜誌以降的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系譜——粗略地說,一個從「意識流」(比如白先勇)到「破中文」(比如王文興)、從腦內泉湧文脈(文學的抽象性)到紙上鉛字排列(文字的物質性)而建構起來的台灣現代主義典範——那麼,此時我們或許也應該想起,同一時代的《劇場》雜誌如何以「文學」去想像「現代主義電影」,如何讓陳映真在現代主義與寫實主義之間左右為難(註17),以及尤其是黃華成的現代主義美學實驗:從「鉛字組裝」作為「圖像」,到「封面設計」作為「文學評論」;從反美學的達達主義,到等待果陀式劇作《先知》的High Modernism;在虛無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之間,在文學與當代藝術之間。對我而言,汪正翔這次由楊逵而起的攝影裝置作品,正是處於楊逵與黃華成之間。(註18)
 「花園裡的一塊磚」展覽講座「重探文獻與影像的檔案,重建楊逵的東海花園」(黃崇凱、汪正翔主講,黃建宏主持)(2025,關渡美術館)。圖片來源: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
「花園裡的一塊磚」展覽講座「重探文獻與影像的檔案,重建楊逵的東海花園」(黃崇凱、汪正翔主講,黃建宏主持)(2025,關渡美術館)。圖片來源: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
結語:拋磚引玉,我有一塊磚
策展人葉杏柔從1990年代影音媒介中的楊逵,在關渡美術館裡重返1970年代的東海花園,讓四位以影音進行創作的當代藝術家,在這座虛擬的花園裡,以各自手裡的「一塊磚」,敲打與重建楊逵的文學空間。李慈湄在藝文園區的藍圖上、同時也在迫遷抗爭的現場,設置了「台灣文學的來世」的入口;黃大旺以當代藝術的語彙(及其雜訊與噪音),展示了如何在美術館裡展示楊逵的文學;劉紀彤透過楊逵的戰友兼室友葉陶,在陌生化的音畫配置裡,讓文學反而得以尖新浮現;汪正翔以反寫實主義傳統的攝影裝置,顯影、對照楊逵如何以寫實文學介入社會現實,如何以小說創作進行左翼實踐。
展覽名稱「花園裡的一塊磚」,來自楊逵在東海花園撰寫的一篇短文〈我有一塊磚〉。於我而言,「磚」不僅僅是簡單直接地描述了當年東海花園現場的具體建材之一;當楊逵在台灣文學史裡的位置與意義已然被安置(甚至被固化)多年,以至於,理應持續因應新的社會時勢而不斷被翻新或謂不斷革命的(楊逵終生抱持的)左翼實踐,其動能已經很久未被開採和汲取了。楊逵所說的「磚」,我認為其實同時也指涉了左翼意義上的「建設」(建造民生基礎設施或下層結構)以及「團結」(作為個體的一塊磚,團結成為一座建築體)。但同時,楊逵在短文裡也提到了一個似乎與「磚塊們集合起來眾志成城」相反的「拋磚引玉」意象,以及「讓東海花園成為藝文基地」的理想,如此,「磚」就成了一種「媒介」,讓人想起了魯迅的「中間物」,一如楊逵〈送報伕〉這篇小說自身、以及小說裡的「報紙=媒介」。
於是,在「花園裡的一塊磚」這個展覽裡,參展藝術家的作品,既是玉(被楊逵的磚所引來),也是磚(拋出去而期待著回應);既是自身完整的作品(藝術自主性),也是作為媒介的中間物(藝術介入社會)。最終,這個「在當代美術館裡展示台灣文學」的展覽,既向台灣文學圈投擲了一塊磚:讓當代藝術也成為台灣文學的來世;同時,也向當代藝術圈投擲了另一塊磚:楊逵的文學及其左翼實踐,值得當代藝術的批判實踐,重新開採。
 「花園裡的一塊磚」展覽(2025,關渡美術館)檔案區。1976年10月21日《中央日報》第十版刊載楊逵〈我有一塊磚〉。圖片來源: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
「花園裡的一塊磚」展覽(2025,關渡美術館)檔案區。1976年10月21日《中央日報》第十版刊載楊逵〈我有一塊磚〉。圖片來源: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
【註解】
註13. 俄國形式主義理論家Viktor Shklovsky所提出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或謂「去熟稔化」的藝術創作手法,指的是:透過藝術處理,讓我們熟悉而習以為常的事物,變得陌生或新穎,因此讓我們對這些事物再次感到新鮮或新奇、進而重新審視它們、最後對它們產生了嶄新的認識或認知。
註14. 這本《楊逵影集》(1992)乃是「楊逵、鍾理和回顧展」的展覽專書,當時展出的照片極豐富,時代跨距1920年代至1980年代,包含楊逵與葉陶的家族照片、生活側拍、楊逵手稿,以及少量以楊逵其人與其作品為題的木刻版畫。
註15. 汪正翔在此處採取的「觀景台」與「風景解說牌」的形式,其實在他稍早的作品「台灣聖山」裡已然出現,可參見以下二篇評論:朱峯誼〈你不曾去過的「台灣聖山」〉(2020)、林運鴻〈沒有景觀的山景《台灣聖山》:我們站在哪裡,才能看見台灣?〉(2020)。
註16. 此處提及的攝影實踐與論述的左翼系譜,乃是汪正翔在「花園裡的一塊磚」展覽座談「重探文獻與影像的檔案,重建楊逵的東海花園」(2025年5月25日)上勾勒出來的。關於攝影的本體論問題,散見於汪正翔平日發表在社群平台、線上刊物、大小雜誌上,他思索「當代藝術」與「攝影」的文章;部份文章已收錄結集出版:《旁觀的方式:從班雅明、桑塔格到自拍、手機攝影與IG,一個台灣斜槓攝影師的影像絮語》,2022三月,臉譜出版社。「重探文獻與影像的檔案,重建楊逵的東海花園」講座介紹可見連結。另外也可參考「花園裡的一塊磚」展覽另一場座談「如何拋磚引玉、重建東海花園⸺媒介與媒體的社會實踐」講座(2025.5.11,主持顧玉玲;講者胡清雅、陳柏謙),這場講座亦談及了左翼與更大範圍的傳播、媒體之間的關係,請見連結。
註17. 關於陳映真在《劇場》裡的左右為難,可參見以下兩篇文章:(1) 陳佳琦〈陳映真與《劇場》的分裂:記一段現代╱鄉土對峙的史前星火〉,刊於《藝術觀點》第41期,2010年一月。(2) 張世倫〈六○年代臺灣青年電影實驗的一些現實主義傾向,及其空缺〉,刊於《藝術觀點》第74期,2018年五月。
註18. 近十年來,當代藝術圈、電影圈、與台灣文學圈,先後開始對《劇場》雜誌以及黃華成的創作萌生了濃厚的興趣,相關研究也持續出爐。2020年於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辦、由張世倫策展的「未完成,黃華成」及其展覽專書,乃是認識黃華成的最佳途徑。
編輯|陳平浩
網站編輯|劉佳旻
本文為2024年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多元藝術專案」贊助。特別感謝「藝術圈圈」合作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