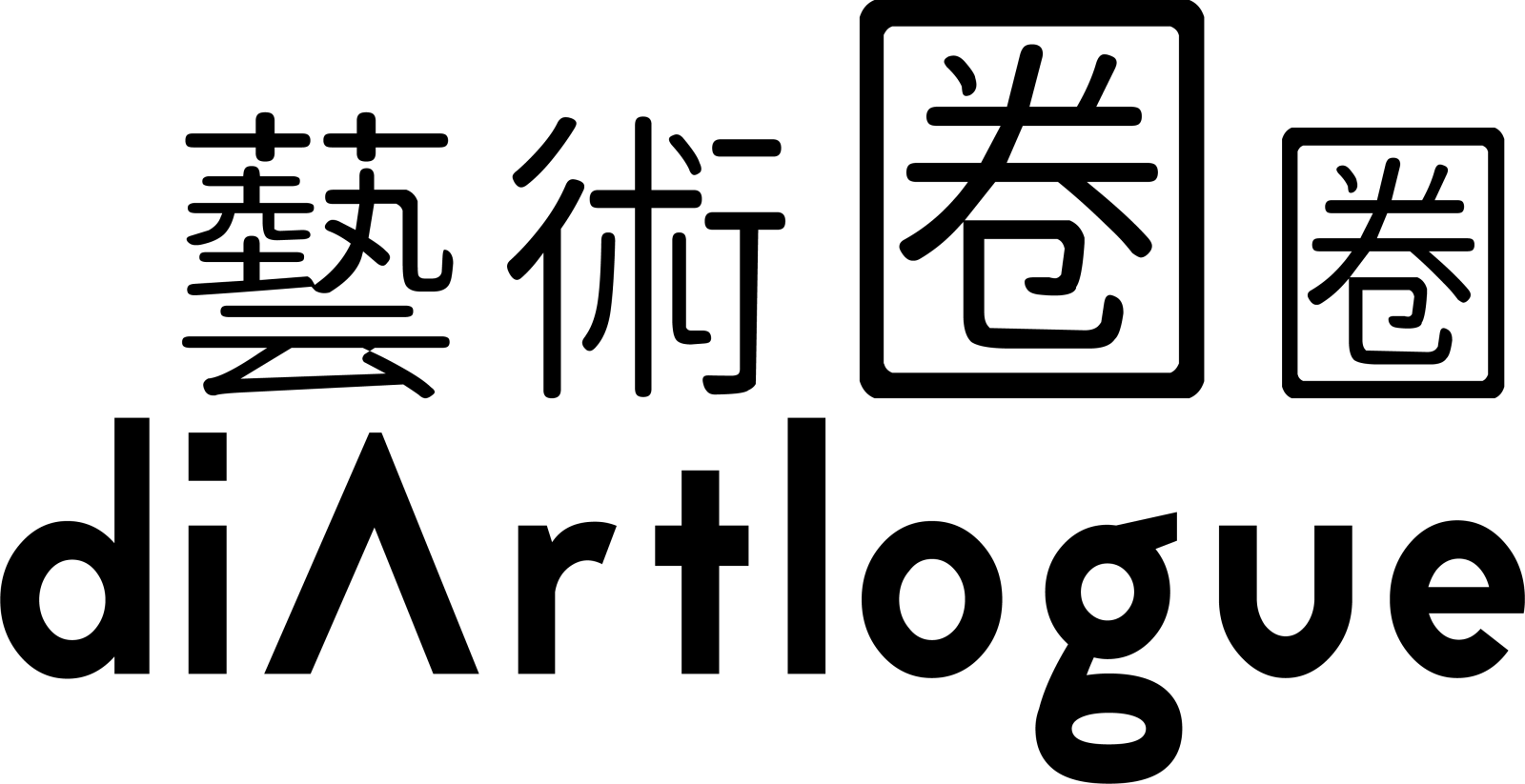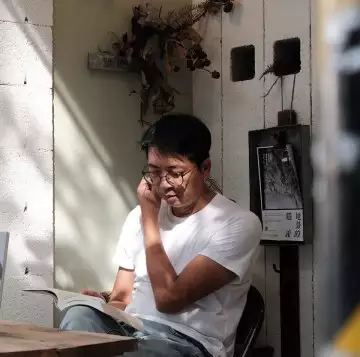- 2025-10-24 19:49:00
文|黃湯姆
新庄子的土地公廟不是我唯一一個指認的地祇所在。
二○二一年四月一日,我到關渡在地建設公司的辦公室解除租約,遇到同事們正煩惱土地廟慶典的問題:本來的小廟到底在哪裡?哪個大伯、哪位叔公說的都不一樣。利用筆電裡的戰時航照,我幫他們指認福壽宮搬遷前、原初的田間位址。
最早的歷史航照研究專著就是在關渡完成的。《反轉戰爭之眼:從美軍舊航照解讀台灣地景脈絡》利用不同時期影像比對流域變遷,翻轉了過去對關渡土壤鹽化的普遍解釋:
「一九六四年行政院核定淡水河防洪治本計畫第一期實施工程,其中包括拓寬關渡隘口並浚渫社子島端河槽。比對戰時航拍與當代衛星影像,淡水河右岸農田因土壤鹽化而廢耕,紅樹林與今日關渡自然公園應運而生;左岸五股洲後村亦遭鹽害,其後更因二重疏洪道工程被迫遷村。民間咸認,炸開關渡隘口致使海水倒灌、良田遭害。
然而,淡水河本是感潮河,潮汐影響直抵淡水,拓寬隘口並非倒灌主因。一九六四年落成的石門水庫攔取水沙、減少下游地下水補注並改變河道水文地形,從而改變原有淡鹹水平衡;且戰後地下水超限利用導致盆地地層下陷、窪地積水不退,同時間的大量河沙抽取亦加劇鹹水侵入。關渡與洲後的命運,實是被更大範圍的現代水沙資源使用所決定,而盆地下陷與沙石難題,則要待到相關管制措施實行後才得以緩解。」
在地居民、比如仙渡莊旅舍老闆深信不已的民間說法雖不能成立,但老闆說故事的動人口吻,讓人理解為何關於地理變遷,人們會是傳播這類人定不能勝天的通俗教化解釋;而相較於常人短時間、眼前所見的單一歸因,航照研究的優勢則是在長時間、跨範圍的觀看。
我在關渡的房子沒有廚房,簡單至極的出租套房,但賃居的前三年,應該是我生命中最平穩的時光。那時身邊的書都還在,每天聽著列車聲響,每天聽著幼稚園聲音朗朗,我專注於某事、有些收入、憂鬱,但很快就會快樂起來,因為就要去見到某人,就要見到某人。
在她最初離開的半年時間,我沒有任何挽回的動作,實是因為她在Instagram的最後一段訊息:「當初怕你死,陪你走到現在,應該不算辜負。」都太過倔強了的我們,我讀到言外之義的拖累,就再也不可能喊她回頭。
她走了,我留在關渡平原。訊息兩天後,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我開始寫字給她,這些字當然沒有傳遞,往後也不會:「如前所述,我終於抵達一處不會下雨的地方。不怕了,不會再害怕了,日子敗壞、腐臭,大街不再有人。
不下雨的地方,在鐵道改線或車頭易址之處。比如你想像得見仙渡莊旅舍旁、破落巷弄盡頭蔓草處,曾是上世紀北淡線關渡車站所在,民族誌裡西河鎮天公角最繁華的道路。比如南港東南街、或更遠更遠之前的中南街,再上個世紀末乘降場的所在。
不下雨的地方,在敘事的反面,在農田與都會的二元之間,無憂亦無怖。如果一處聚落地景經過二次以上塗覆,人們就不可能找得到,它會消失在新時代的通俗敘事市井傳布裡,人棄於地、人浮如鬼,人終止於話語裡。
於是這天早上我醒來,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自己何以在此。洗衣水流過路面,但大街不再有人,日常中止,擱淺於五○年代的南港,或隱姓埋名的西河。」
跟她在一起,我慢慢變成不怕下雨的人,可以想像家的人。離開她,我成了擱淺的人、終止在話語裡的人。愛別離苦,田野步行無用;分離三個月後,我尋求當代醫療的協助:
重掛十五年前的門診,但兩點半了,舒國治都走完了美國。離開醫院去保德宮找展,走平原圳路與貴水大排,比人高的草叢、廢棄的工寮。父親打來問無事否。好,吃飽了。酒吧有隻漂亮親人的大狗。little girl,主人說。中山北路七段,人一生會念念不忘的有:毋甘。毋甘願。
——〈關渡平原〉(2022)
那天中午前讀完的書是《遙遠的公路》,平原上的展覽是「流浪的土地公:北投社保德宮的神明地誌學」,毋甘,毋甘願,而我字無法成篇,但仍以詩強記之。日後終於成功去到門診,初次的問診內容記得有:
——這些年你怎麼度過的。
——伴侶以及走路。(筆記……)
——有人知道你們的交往嗎。
——嗯,大約三四個。(筆記……)
——所以你有人可以傾吐分離的狀況嗎。
——嗯,沒有,沒有人。(筆記……)
當代社會地景大規模改易,庄頭解構、信仰離散,我們的愛,只是平原上的小小水滴。看航照的人,要怎麼看到自身的盲點。就只能任她漸行漸遠,忍受疼痛,以為一切都有盡頭。
每次正午離開關渡醫院,我都想著要去河邊。無論是拓寬隘口、無論漲潮退潮、無論是地層下陷,無人在乎、無人知曉的我們的愛情,我都想著要去河邊。有人知道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嗎?有人傾吐就會更好嗎?念念不忘的是捨不得、還是不甘願?我在一個完全孤獨的地界中,依賴藥物,掙扎泅泳。
二○二○年最後一個月,我每天醒時會看Facebook的動態回顧。經年的頹喪,把廢或中二進行到底,有些行為或字詞會顯現不同意義。去年的乾麵、饅頭或豆花,某天她跟我說的話,某個夢,某個決定,某棵海棗。比如四年前的元旦,我要離開紅樹林;比如十年前的元旦,我打算到花蓮上學。
二○二一年第三天的夢。我離開城市裡的婚宴般的場合,說想往烏日的方向走,想去看油井。實際抵達是一處高地的塵土路口,亞洲市鎮街邊溝渠有的正開挖、有的已燃燒。有同伴隨來,她們好奇、想跟我看看。敵意的怪手把我們逼到牆角,履帶前沿壓迫肉身胸腔、四肢埋入。同伴逐一被不同語言的男人抬走,我知道將發生傷害。
噩夢不是現實的壓力,但我已知它反映想觀看、想發聲,此行為的自我中心,以及我對群體與社會的失能。把它記著,幾年後廢墟重遊,我或許還會讀到什麼。噩夢也無關日常的情緒狀態。連假那幾天我完全沒工作,即便看照片或地圖,也是很遠的地方很遠的事件,比如海外宣道會百年前的旅行,比如荷蘭某河某橋。信箱裡積了好幾件事,天氣冷到走路會打顫。
該是時候了,我在Facebook貼出(她會看得到,我也預期她會看到):「跨過去的這個年,像是終於跨過這條河,抵達未知的埔地,我想要開墾、想要搭建,四時風景、日升日落。謝謝過去這起伏的一年中,協助、照看過我的人。謝謝領我走過現代、穿過山谷來到岸邊的某人。我到了,一切安好,未來開始。」
就這樣結束了嗎。我以為就這樣結束了,抵達未知的埔地,可以遇見新的人了,可以開始新的人生了。但一切都跟我以為的截然不同:她一直在等我,在更暗更暗的地方,她一直在等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