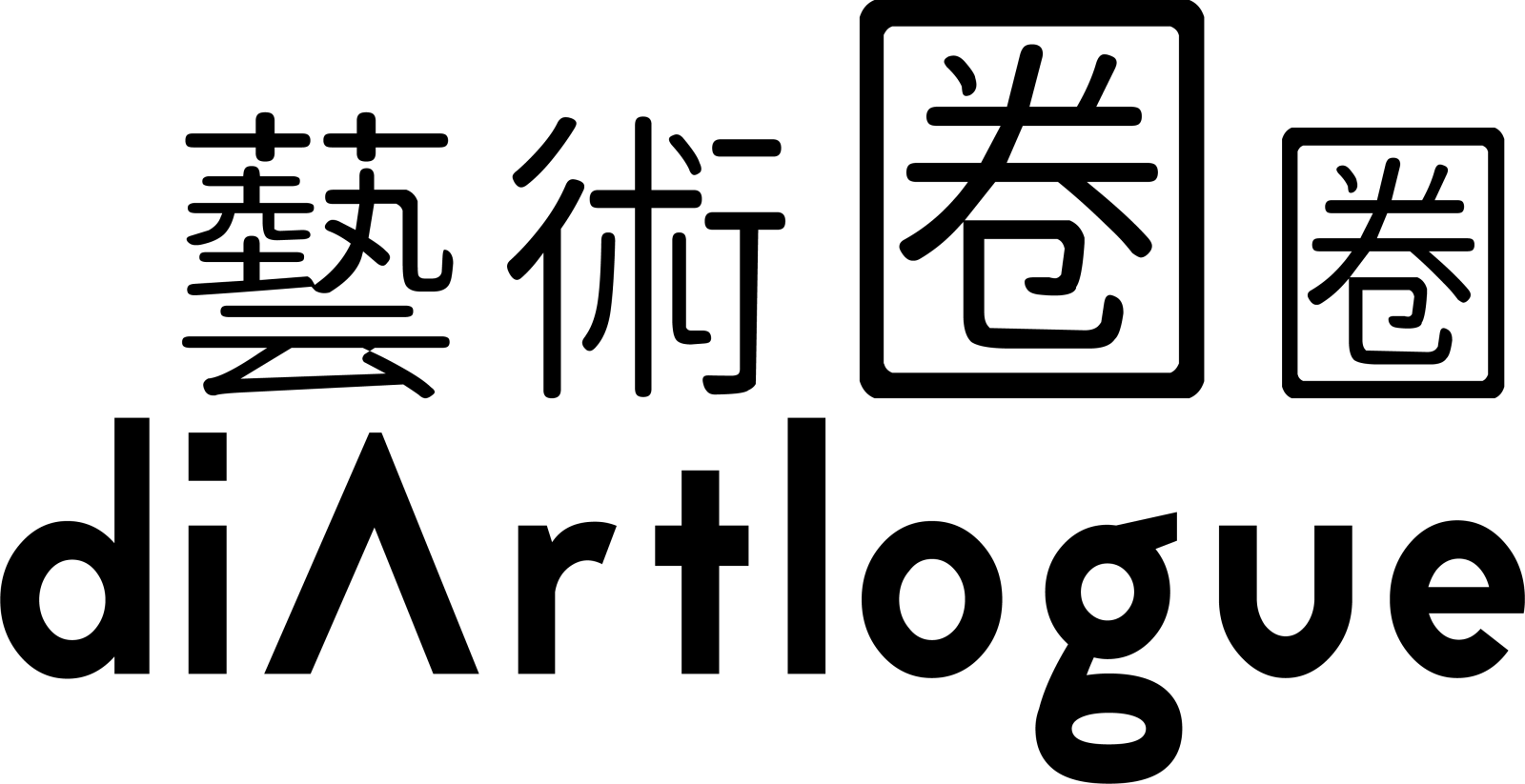- 2025-10-19 19:07:00
文|林沛瑤
一場訪談或是一部紀錄片,讓人最難以置信的,時常不是導演實際上拍下了什麼、影像內發生了什麼事,而是一個更為直接的疑問:這些究竟是用什麼方式、在什麼情境下被記錄下來的?
一件非虛構作品最吸引人的,常常是記錄者與被記錄者之間的關係。尤其當兩者之間還有著其他緊密的身份羈絆,纏繞、疊加在記錄的關係之上,像是朋友、師生、情人或家人。鬆動鏡頭意識的往往是奠基於關係的情感,與攝影機原生的侵略性相互衝突,進而使距離感產生變化。
話雖如此,張庭甄的作品幾乎沒有以攝影機直接拍攝人物對象。展覽同名作品《藍門後的光》(2025)以其對檔案——包含家人的老照片、3D掃描模型、訪談父親的音檔——的反覆操作與玩轉,以及可視卻不可觸及、步入的雙層投影空間,為觀眾創造出有別於一般紀錄片觀看的獨特身體感。 張庭甄,《藍門後的光》,雙層投影雙頻道錄像裝置,21 分循環 ,2025。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
張庭甄,《藍門後的光》,雙層投影雙頻道錄像裝置,21 分循環 ,2025。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
接觸檔案的身體感
《藍門後的光》從舊家屋3D掃描模型的畫面開始,因為現場的光線不足,模型顯得有些殘破。影像以無重力的視角,帶領觀者徜徉於藍色門扇後,耳畔同時響起藝術家父親的聲音,舊地重遊般地介紹祖父的舊家屋。
這是父親長大的房子,即將轉售他人,而掃描記錄下來的是交屋的前一天。從家屋的歷史沿革開始娓娓道來,父親敘述著小時候家裡的舊格局、空地曾種植的果樹,再到因道路拓寬徵收而必須調整房屋格局的「舉厝」(1)過程。有趣的是,已化為模型的屋子,在影像中能夠被藝術家輕易地穿孔、抬升與轉動,然而可以想像當年絕對非常費力,形成身體感的殊異反差。
在2022年的兩件作品《那一天,風光明媚》與《你直得被愛》中,張庭甄將「手」作為介入影像的重要媒介。(2)前者輕輕拾起家庭影像,以手指在照片表面游移撫觸;後者則以手執刀具切割兒時照片,使開展的雙臂如索取擁抱一般向前彎折。到了《藍門後的光》,接觸開始由類比轉為數位,滑鼠游標成為手與檔案接觸的另一層媒介,與檔案「接觸」的身體感也隨之變化。 張庭甄,《那一天,風光明媚》,雙頻道錄像,30’55” 循環播放,2022。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
張庭甄,《那一天,風光明媚》,雙頻道錄像,30’55” 循環播放,2022。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
 張庭甄,《你直得被愛》,家庭照片數位輸出、大理 石、鋁、抽屜,8.9 × 12.7 cm,四件 / 10.2 × 15.2 cm, 二件,2022。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除了影像以外,細膩的字幕運用也是這件作品的重要元素之一。前方頻道的影像與字幕,由後往前投影在紗幕上,同時透出光線倒映於地板。隨著敘事行進,投影在後方牆面的影像——例如以3D建模重現的、爸爸由高筒皮靴修剪而成的短筒皮鞋——會與前方嘉義高中學生穿著皮鞋的歷史照片重疊;偶爾,後方的影像也會完全消失,黑暗將紗幕內的空間再度壓縮為一個平面,變回一個電腦桌面。
張庭甄,《你直得被愛》,家庭照片數位輸出、大理 石、鋁、抽屜,8.9 × 12.7 cm,四件 / 10.2 × 15.2 cm, 二件,2022。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除了影像以外,細膩的字幕運用也是這件作品的重要元素之一。前方頻道的影像與字幕,由後往前投影在紗幕上,同時透出光線倒映於地板。隨著敘事行進,投影在後方牆面的影像——例如以3D建模重現的、爸爸由高筒皮靴修剪而成的短筒皮鞋——會與前方嘉義高中學生穿著皮鞋的歷史照片重疊;偶爾,後方的影像也會完全消失,黑暗將紗幕內的空間再度壓縮為一個平面,變回一個電腦桌面。
不過,與其說特別聚焦在數位影像檔案的操作,藝術家曾提到這次創作的起源,更多是關於「3D掃描」這個技術。例如在電腦軟體編輯3D掃描檔案時,放大、縮小、旋轉等介入檔案的動作,創造了相當獨特的身體感,對她來說是一種「既立體又不立體」的感覺。 張庭甄,《藍門後的光》,雙層投影雙頻道錄像裝 置,21 分循環 ,2025。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
張庭甄,《藍門後的光》,雙層投影雙頻道錄像裝 置,21 分循環 ,2025。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
 張庭甄,《藍門後的光》,雙層投影雙頻道錄像裝 置,21 分循環 ,2025。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臨場的距離感:家人間的情感張力
張庭甄,《藍門後的光》,雙層投影雙頻道錄像裝 置,21 分循環 ,2025。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臨場的距離感:家人間的情感張力
「既立體又不立體」不失為一個相當精準的描述,相當貼合觀展時的體驗。一方面,現場的雙層投影打造了一個可見卻無法實際進入的立體空間,一如3D軟體提供的環境,創造了一種臨場的距離感;在情感層面,除了影像自身的陌生化特性之外,我認為在張庭甄的作品中,那種親密又疏離的印象還有另一層背景,是藝術家同時作為作者與家庭成員,兩種身份疊加所創造出來的雙重距離。
觀影的當下,作品後半段中的一段父女對話令人感到好奇。除了因為原本的敘事核心都是關於祖父與父親,更因為在這段對話中,藝術家將自己的回應以無聲的字幕呈現,父親則維持有聲。這不禁讓我猜想,女兒的這段回應,在訪談當下是否真實發生?或其實這是一份遲至的跨時空對話?這份靜默牽引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權力關係,其一是父親的權威,女兒在對話當下只能沉默聆聽;其二則是作者編纂的權力——父親的回應被「真實地」以錄音呈現,而女兒的回應則因為字幕的形式,被推向一種介於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狀態:不論究竟真實與否,都已經染上了虛構的色彩。
日後庭甄說明,這段對話是不預期的,自己在當下回應的內容也確實如字幕所呈現;不過在決定放入此段落後,之所以讓自己靜音,除了希望讓父親作為整件作品聲音詮釋的主體,也因為這段「對話」其實稱不上有效的溝通。爸爸對自己的就學與職涯期待,與祖父對其兒女的期待,或多或少都反應了祖父自身因家道中落未能赴日學醫的遺憾,以及臺灣不同世代之間,對於兒女或是自身理想生活樣貌的期許。
作為作者,她將父親的話語錄音,同時以女兒的身份聆聽;作為女兒,她將自己對父親的回應去除聲音、只留下文字,同時擔任編纂敘事的作者。緊接著,庭甄的聲音首次粉墨登場——卻是在父女對話業已結束之後,只留下兩個發音相似的詞語:「唸書」與「思念」,迴盪在空間中,陪伴著以字幕補述的無聲內心旁白。此後,父親的聲音從敘述者退位,女兒卻也並不完全接手這個位置,只是偶爾說上幾句話,讓觀者在閱讀字幕的過程中穿插著聆聽。
我相當好奇,究竟是在什麼樣的訪問情境下,父親能夠如此繪聲繪影地描述其記憶的細節?是在交屋前一天回到現場時錄下的嗎?還是女兒讓父親一面看著房子的3D模型,一面邀請他進行一場虛擬導覽?或純粹是憑空回憶?儘管對走藝術這條路略有微詞,他還是以其飽滿的情感,將自己全然交付,參與了女兒的作品。相較之下,庭甄的聲音冷靜、不帶情感而自持,與父親相差甚遠,後半段也因此讓人感到趨於靜默,為這段似乎未竟的對話留下懸念。
一方面,這段對話挑起了我對於戲劇性的期待,因此這邊的突然作結,讓我感到些微落空;另一方面,這些距離卻也留下了不同於許多紀錄片的另類情感張力。例如不以攝影機拍攝舊家屋,而是用螢幕錄影錄下在家屋3D模型中的「移動」;呈現父親的聲音、但不直接拍攝父親(3);或者以無聲的文字,取代自己說話的聲音。這樣相對間接的呈現手法,少了攝影機試圖迫近對象的直截了當,卻如那道投影紗幕般立起了一道屏障;即便被其吸引,我們也難以實際靠近。 張庭甄,《藍門後的光》,雙層投影雙頻道錄像裝 置,21 分循環 ,2025。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
張庭甄,《藍門後的光》,雙層投影雙頻道錄像裝 置,21 分循環 ,2025。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
 張庭甄,《藍門後的光》,雙層投影雙頻道錄像裝 置,21 分循環 ,2025。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可觸及的光,不可觸及的印象
張庭甄,《藍門後的光》,雙層投影雙頻道錄像裝 置,21 分循環 ,2025。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可觸及的光,不可觸及的印象
這樣隱微的張力並非藝術家對自身情感的刻意壓抑。一方面,或許是藝術家自身性格加上家人關係的自然反映;另一方面,則與記憶/印象的不穩定性,以及對此不穩定性的著迷有關。在《那一天,風光明媚》和《你直得被愛》(2022)中,令藝術家感到陌生的是兒時爽朗熱情的自己、尚未婚的母親優雅的形象,那些是對熟悉的人事物感到陌生的時刻;《藍門後的光》則從舊家屋與舊檔案的清理開始,隨著對陌生的祖父有了更多的理解,也逐漸找到一些與過往印象相衝突的資訊。例如,明明記得大家都稱祖父為「張校長」,在其曾任職的三間國小的歷任校長名單中,卻遍尋不著祖父的名字;明明父親與自己印象中的祖父相當地嚴厲、「很兇」,但在國小的教職員合照中,祖父的雙臂卻被隔壁的兩位推擠至後,如錄像中字幕所述,「彷彿替換成了鄰座的肩膀」。
在不可觸及的距離之下,「光」作為人與檔案得以產生聯繫的媒介,在這檔展覽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藍色門扇後的光,乘載了對舊家屋與往昔人事物的印象;舊照片裡留存的光線,再現了或熟悉或陌生的印象,並經由數位化成為照亮展場的投影光。除了重現與編輯以外,藝術家還進一步改造檔案,透過人工智慧將大合照的人物運算為3D模型,再列印為透明的雕塑。原本不透明、透過反射光顯影在照片中的祖父形象,自此能夠被任何光線所穿透,不再映照出堅實而穩定的單一形象,經虛構後反而更顯真實。
然而,除了難以實際觸及的過去時光與往日印象,藝術家也將自己對於興趣乃至於創作追求的自白,低調而簡短地加入其中,短暫地讓敘事的鎂光燈照亮了自己。如同雙層投影裝置的背投影像偶爾將光線「送出來」,我們短暫地觸及了這些檔案與故事,並在展覽現場為它所照亮。 張庭甄,《掃描一扇目光》,玻璃噴墨輸出,30 x 26 cm(一式 12 件),2025。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
張庭甄,《掃描一扇目光》,玻璃噴墨輸出,30 x 26 cm(一式 12 件),2025。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
 張庭甄,《正像》,SLA 光敏樹脂 3D 列印,30 × 14 × 17 cm,2025。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____________
張庭甄,《正像》,SLA 光敏樹脂 3D 列印,30 × 14 × 17 cm,2025。圖片來源:藝術家提供。____________
(1)臺語,音khíng-tshù,意指將房子整體抬高。
(2)引自張庭甄《你直得被愛》創作自述。
(3)至於那難得的例外——實際拍攝父親打領帶的片段,卻又將父親的臉部遮去,以其年輕時的照片取代。比起記錄,我感到這更像是一小段表演,或許就跟這段如天外飛來一筆的父女對話一樣,其間距離的拿捏與張力耐人尋味。